文|付桂香
巷口的泡桐树总在暮春时节落花。淡紫的喇叭状花朵扑簌簌跌在老榆木桌上,给褪色的《水浒传》封面缀满星星。燕青的皂靴踩着零落的花瓣,在风里簌簌作响,仿佛下一刻就要踏出泛黄的纸页。这方寸天地,是王爷爷守了四十年的江湖。
晨雾未散时,老人佝偻的身影便出现在树下。褪色的蓝布衫口袋里,总揣着半块油纸包的桃酥,碎屑落在翻动书页的指缝间。他擦拭书封的动作像在抚摸婴孩,起毛的袖口拂过《说唐》里秦琼的鎏金锏,惊起几粒细小的尘埃,在朝阳里跳着碎金般的舞。街坊说这书摊原是他妻子陪嫁的妆奁改的,自她走后,那些泛黄的书页便成了续命的汤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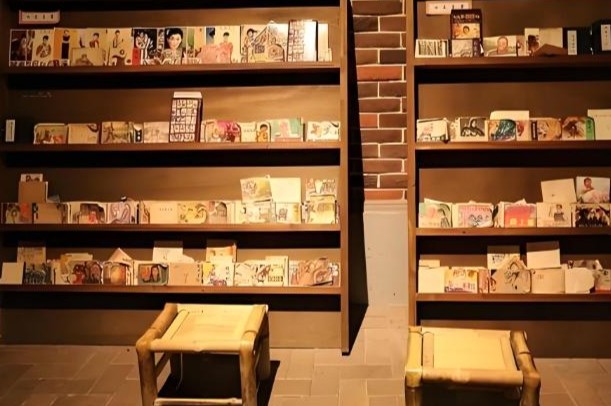
放学的铃声未散尽,青石板上便滚来细碎的脚步声。七八个五颜六色的布书包挤在桌前,手指悬在书脊上方游移,像在琴键上寻找音符。王爷爷的竹烟杆敲了敲藤椅扶手:“别抢别抢,关二爷的赤兔马跑不脱。”孩子们咯咯笑着,翻捡起各自的心头好,蜷在墙根的条石边,任斜阳把影子拉得老长。砖缝里的青苔沾着我们的体温,渐渐洇成墨绿的云纹。
我最爱那套《西游》,黄裱纸沁着油墨的沉香。孙悟空的金箍棒总在第九页扫出裂帛之势,我疑心下一页纸要被挑破。指腹摩挲过五指山压着的猴头时,会触到前个读者留下的汗渍,薄脆的纸页上叠着层层叠叠的指纹。隔壁二胖捧着《说岳全传》抹眼泪,鼻涕泡在“风波亭”那章破了三回,咸涩的水珠晕开了“天日昭昭”的墨迹。小玉攥着《红楼梦》的边角发怔,她总说林妹妹的衣袂在风里会飘出茉莉香,说着便把书页贴近鼻尖,睫毛在瓷白的脸上投下颤动的影子。
王爷爷的茶缸搁在桌角,搪瓷剥落处露出锈色的伤痕。茉莉花茶淡了又续,浮沉的茶梗像极了《镜花缘》里漂洋过海的小船。他的老花镜滑到鼻尖,目光却越过镜框,看着我们头顶的泡桐花落在书页间。有时我会摸出块麦芽糖,掰成参差的几块,甜味裹着油墨香,在齿间缠成解不开的结。糖渣嵌进《封神榜》里姜子牙的鱼竿纹路,倒像是给直钩缀上了琥珀色的饵。

惊蛰的雷鸣劈开料峭春寒时,二胖失手将《聊斋》跌进泥淖。聂小倩素白裙裾溅上了斑驳泥痕,倒比兰若寺更多三分人间烟火。泛潮的空气里,《牡丹亭》的游园惊梦正在氤氲,杜丽娘的水袖在纸面霉斑间舒卷,仿佛下一秒就要甩出隔世梅香。
夏雨垂帘时,油布篷鼓荡成透明的蛙鸣。我们蜷在《白蛇传》的褶皱间,看许仙的伞面在雨幕里化开青灰色墨团。断桥石缝渗下的雨帘中,白娘子鬓边绒花褪成经年茶渍,雷峰塔的倒影在积水里晃出万道金芒。
霜降为旧书摊披上柿色袈裟,《西游记》里的火焰山在落叶堆里明明暗暗。孙悟空的金箍棒挑着糖炒栗子的焦香,猪八戒的钉耙上栖着南迁的雁阵。我们踩着满地《红楼梦》的蟹壳青吟诗句,看史湘云的石凳凝满白霜,黛玉的药吊子腾起桂花味的轻烟。
腊月的炭盆哔剥作响时,《哪吒闹海》在火光中重生。敖丙的银甲折射着橘色暖芒,混天绫在热气里翻涌成糖瓜的脆响。王爷爷的火钳拨动《封神演义》,沉香木烟絮缠绕着我们的呵气,将东海龙宫熔成掌心一块滚烫的烤红薯。 前年深秋回去,老桌还在树下,覆着层薄灰。几片枯叶卡在《三国演义》的夹页里,诸葛亮手中的羽扇缺了半截,摇出的东风终究没能吹散岁月的尘埃。风起时,书页翻动的簌簌声,恍若当年此起彼伏的抽气声——那是看到赵子龙单骑救主时七八个孩子同时倒吸的凉气,在时光里凝成了霜。巷尾飘来新开铺子里的奶茶香,却再没有茉莉花茶混着麦芽糖的滋味,古旧的油墨气被香精冲得七零八落。
而今在古籍市场偶见品相完好的小人书,细绫装裱,锁在玻璃柜里。可我还是想念卷边的书角,想念二胖的鼻涕泡落在《精忠报国》字样上的模样。那些被无数小手抚出毛边的故事,在岁月里酿成了琥珀,裹着泡桐花的影子和炭火的噼啪声,永远停在巷口那抹斜阳里。有时午夜梦回,依稀听见竹烟杆敲在藤椅扶手上的脆响,睁开眼,却只见月光在精装书烫金标题上流淌,冷冰冰地映着现代印刷术完美的网格线。
旧城改造通知贴在泡桐树上的那天,王爷爷把最后一本《西游》塞进我怀里。书脊的棉线早已松散,每一页都住着不同的四季——春天夹着紫藤花瓣,夏天渗着西瓜渍,秋天粘着桂花屑,冬天凝着冰糖霜。现在它躺在我檀木箱的最底层,每次翻开,仍有细小的时光碎屑落在膝头,像那年暮春不肯凋零的泡桐花。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山东省作协会员)




热门评论 我要评论 微信扫码
移动端评论
暂无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