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张儒学
瓦是泥土做的,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月,依然散发着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我刚去城里打工时,没有自己的房子,只租了一间小屋。等我回到乡下老家,二叔拉着我手说:“大娃,你得努力工作,多挣点钱,好在县城买房子,不然你在城里打拼这么多年,连一块瓦片都没有。”我知道,二叔说的瓦片是指房子。在人们眼中,有了瓦就有了房子,有了房子就有了根,我才能在县城待下去。
听二叔这么一说,我似乎明白了瓦的含义和分量。不管在城市或乡村,许多楼顶上都盖着一片片青瓦,那些泥土做的瓦看似不言不语,却以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姿态,见证了无数个日升月落,守望过多少春秋。每当夕阳西下,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些瓦片上,给它们染上了温馨而美好的色彩。屋顶上一片片排列有序的瓦,似乎还留下了岁月的痕迹,也编织着五彩斑斓的梦幻。

二叔是个瓦匠,做泥瓦的手艺还算不错。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,灵巧地塑造着一片片青色的瓦,用他的技艺为村庄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景。他不但去过云南、贵州做瓦工手艺,还走村串户给村民烧窑做瓦,村里很多房子的瓦都是他亲手烧出来的。二叔是个手艺人,每天奔忙于村民家中做瓦工,收的那点工钱也不多,别人家修起了高大的瓦房,二叔家仍是几间土墙房。可二叔似乎不在乎这些,仿佛这瓦工手艺才是他的最爱,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活,他就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那天,二叔因家庭琐事和二娘吵嘴,平时不管二娘说什么他都不生气,可那天二娘说了一句:“你看看别人,不是出去打工就是经商,都挣钱了,你还干着这个破瓦匠活儿,有啥用?”就是这么一句话,似乎刺激到了二叔的尊严。二叔气得一时说不出话,一把拉着二娘到屋后的小山坡上,指着村里一幢幢新修的瓦房,大声说:“你看那些房子,哪家不是盖的我做的瓦?”二娘不依不饶地说:“你能干,你行,你怎么不把咱们家那土墙房修成大瓦房呢?”
这下,二叔真被气急了,他一整天都没有回家,坐在小山坡上看着房子上的瓦。此时,那些瓦虽然好看,却没让他高兴起来,反而让他看出了泪水……后来,二叔动了心思、下了决心自己当老板做瓦卖。说干就干,他请人帮忙打起了瓦窑,自己做瓦自己烧窑。村里村外要修房子的人家就来二叔家买瓦,这样二叔收入高了。没几年,二叔挣钱了,他也修起了几间房子,而且修得很漂亮。尤其是房子上的那些瓦,似乎也更好看。
没事时,二叔总是坐在院坝里看自己房子上的瓦,觉得这高高大大的砖瓦房,就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,修得比别人的房子漂亮。这房子之所以漂亮,是因为他房子上的瓦做得好,更是烧得好,青青的,还泛着幽蓝的亮色。每当晨曦初露,或者夕阳西下,他觉得房子上的瓦就像一件件艺术品,怎么看都很美,在阳光或者月光下,闪烁着美丽的光芒。

我每次回乡下老家,二叔总要叫我去他家喝酒,只要两杯酒一下肚,二叔说的话也多起来,他说:“村里人个个都说我的房子修得漂亮,你说我这房子真的漂亮吗?”我说:“二叔,你这房子修得这么高大,也宽敞,当然算是村里修得最好的房子了。”二叔听我这么说更高兴了,又喝了一口酒说:“我这房子之所以修得这么好,是因为这房子上的瓦是我亲手做出来的,瓦好房子当然就变得漂亮了。”我说:“那是,二叔做泥瓦的手艺当然是一流的。”二叔又说:“自己房子上盖着自己做的瓦,别说住在房子心里有多踏实,就是每天看着这房子上的瓦都开心。”晚上,二叔还叫我就在他家住,虽然二叔嘴上没说,但我心里也明白,二叔的意思是他房子修得漂亮,屋子也当然收拾得干净些,我睡在二叔家更舒服。
多年后,我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。不知道开发商是为了提高品位,还是别出心裁,我那个小区房顶上盖的都是瓦。那天,二叔来我家作客,他站在阳台上向外望,就看见对面几幢楼上的瓦。他看了好一阵,有些纳闷:“你看那些瓦,怎么是红色的,没用窑烧就盖在房子上?”我说:“二叔,那些瓦是琉璃瓦,琉璃瓦不是像你做的泥瓦,用柴火烧出来的,那是钢化了瓦,是工艺品。”二叔叹息一声说:“要是这些房子盖上我做的泥瓦,肯定比盖这些瓦更好看。”
去年,二娘去了外地县城带外甥,二叔说什么也不愿意去,就一个人住在乡下瓦房里。那个周末,我回乡下老家,习惯性地去二叔家看他,二叔虽然年过七旬,但身体还很好。那晚,我陪二叔喝了几杯酒,二叔仍叫我在家里住。现在乡村好多房子都变成了两层或三层的楼房,房顶上也几乎不盖瓦了,似乎只有少数像二叔家这样的老房子还盖着泥瓦。
晚饭后,我和二叔在院坝里喝茶聊天,我问道:“二叔,二娘都去你女儿家了,你怎么不去呢?”二叔说:“我得守着我这几间老房子呀,因为这房子上盖着我亲手做的瓦。”我听后,明白了二叔的意思,抬头看了看他房子上的瓦。那些瓦在明亮的月光映照下,像是被露水滋润过的宝石,晶莹剔透,散发着岁月的光泽,温暖而柔和,宁静而淡然……
(作者为重庆市作协会员,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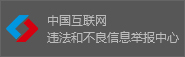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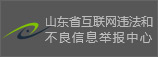
热门评论 我要评论 微信扫码
移动端评论
暂无评论